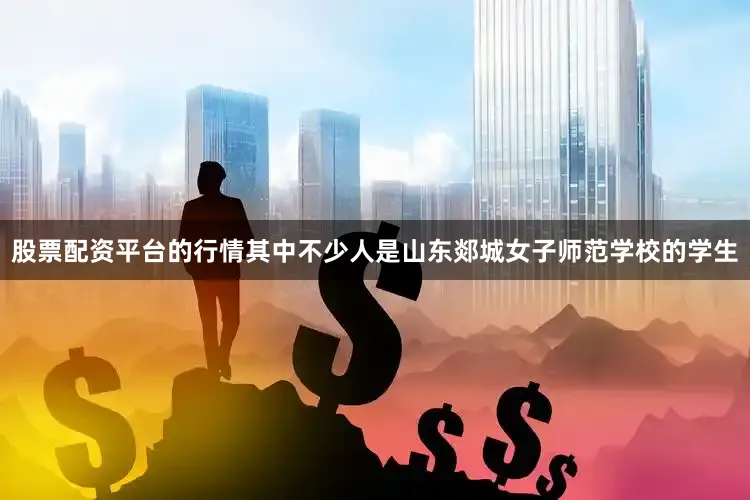
原华东野战军6纵司令部作战科长恽前程在回忆起淮海战役时,曾讲述过黄百韬在运河上控制铁路桥的情景。黄百韬为防止敌方渗透,实行了严格的军事管制,不允许百姓过桥。但即便如此,百姓依然蜂拥而上,几乎不理会阻止的命令。国民党军则在桥上设下机枪,向人群扫射,造成了大量死伤。其中不少人是山东郯城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,正在南迁的她们穿着统一的校服,大多数不过十几岁。很多学生就在桥上丧命,被国民党士兵拖动着、抬着,毫不留情地扔进了河中,现场景象惨烈至极。这一幕至今依然刻骨铭心,成为了许多人难以忘却的痛苦记忆。
1948年11月4日,华东野战军发布了淮海战役的攻击命令,正式拉开了这场决定性战役的序幕。令人意外的是,就在11月5日,徐州“剿总”却在军事会议上发布了撤退命令,决定放弃陇海铁路上的防线,并将兵力集中在徐州和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沿线,实施攻势防御。顾祝同和刘峙认为,华东野战军刚刚结束济南战役,主力部队必然处于休整期,至少在半个月内不会展开大规模进攻。然而,令他们未曾料到的是,华东野战军的部队已经悄然进入了攻势准备阶段,随时准备迎接决战。
展开剩余84%就这样,国共两军几乎在同一时刻展开了不同的战略行动——一方收缩,一方进攻。随着11月6日华东野战军的13个纵队分道扬镳,兵锋直指驻守在新安镇的黄百韬第7兵团,淮海战役的首个大规模冲突正式爆发。
黄百韬的第7兵团驻扎在新安镇,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新安镇位于陇海铁路东段,距离徐州约100公里,是苏北的交通要冲。沿陇海路,从西到东,国民党三大兵团排开。李弥的第13兵团位于曹八集,李延年的第16兵团和第9绥靖区则驻扎在海州,而黄百韬的第7兵团位居中间,是实力最强的一个兵团。表面上看,这样的部署似乎很安全,但实际上,第7兵团却成了华东野战军的首要打击目标。
黄百韬出生在天津,原籍广东梅县,经历了多次军事阵营的转换。他曾在北洋军阀下当兵,后被张宗昌收养,在直奉战争后投奔蒋介石,成为他忠诚的部下。凭借严格的自律和坚定的信念,黄百韬逐步从一个低级军官升至兵团司令。他的忠诚和勇敢深得蒋介石的青睐,屡次获得晋升和嘉奖。
尤其是在1948年6月的豫东战役中,黄百韬坚守帝丘店,面对华东野战军的重重围攻,顽强抵抗,未被突破。蒋介石甚至亲自给他佩戴青天白日勋章,表彰他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。而当华东野战军攻占济南后,黄百韬就预感到,自己的第7兵团将是下一目标。
尽管黄百韬多次向徐州“剿总”发出警告,建议提前集结兵力防守,但当时的刘峙并未采纳。他坚持认为,将各兵团按一字长蛇阵排开,进行防守即可,甚至美其名曰“同进同退”。结果,黄百韬的预感成真,徐州“剿总”发布撤退命令时,第7兵团却被留在了新安镇,面临极大的危险。
黄百韬虽然兵力雄厚,但他深知,如果继续待在新安镇,必定会成为华东野战军的攻击目标。此时,第7兵团的上级命令又让他处于两难境地——他必须等待44军到达新安镇后才能撤退,而这个决定让他深感不安。
一线官兵也敏锐地察觉到战斗即将爆发。原第7兵团100军的连长郭国威回忆起撤退时的情景,甚至看到老百姓家中堆满了地瓜,他敏锐地意识到,这些粮食可能是为即将到来的共军准备的,但上级却并未重视这些迹象。
当第7兵团在新安镇等待的日子越来越久,黄百韬多次与刘峙沟通,急切地询问44军何时能到达,但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。黄百韬感到自己被孤立无援,在这种情况下,他甚至找到了国防部派驻的战地视察官李以劻,希望他能够带消息给蒋介石,争取援兵。
11月7日,44军终于赶到新安镇,黄百韬决定立即命令部队撤退。新安镇距离徐州仅100公里,但当时华东野战军的部队已经迅速逼近,准备在新安镇展开围歼战。第7兵团的撤退过程异常混乱,士兵们与当地百姓混杂在一起,争先恐后地过桥,造成了严重的踩踏事件,许多人因此丧命。黄百韬尽管下令不许百姓过桥,但面对狂乱的民众,命令显得毫无作用,桥上变成了一片血海。
随着华东野战军的追击,黄百韬的兵团陷入了更加严峻的困境。华东野战军的9纵首先赶到新安镇,并发现黄百韬的主力已撤离,整个镇子已经成为空城。这一失误几乎让华东野战军的作战计划陷入停滞,但粟裕代司令员并未放弃,命令部队连夜追击,确保将黄百韬彻底围困。
11月8日,华东野战军9纵与黄百韬第7兵团的后卫部队展开了激烈交火,经过数日追击,最终迫使黄百韬的兵团进入了碾庄圩的围困圈。
尽管黄百韬的兵团在淮海战役中拼死抵抗,但面对华东野战军的全面围剿,第7兵团的覆灭几乎已成定局。
发布于:天津市振兴配资-炒股配资官网查询-证券股票配资-郑州配资网站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股票配资资讯网站
- 下一篇:股票网上配资最早可能在2026年初获得批准



